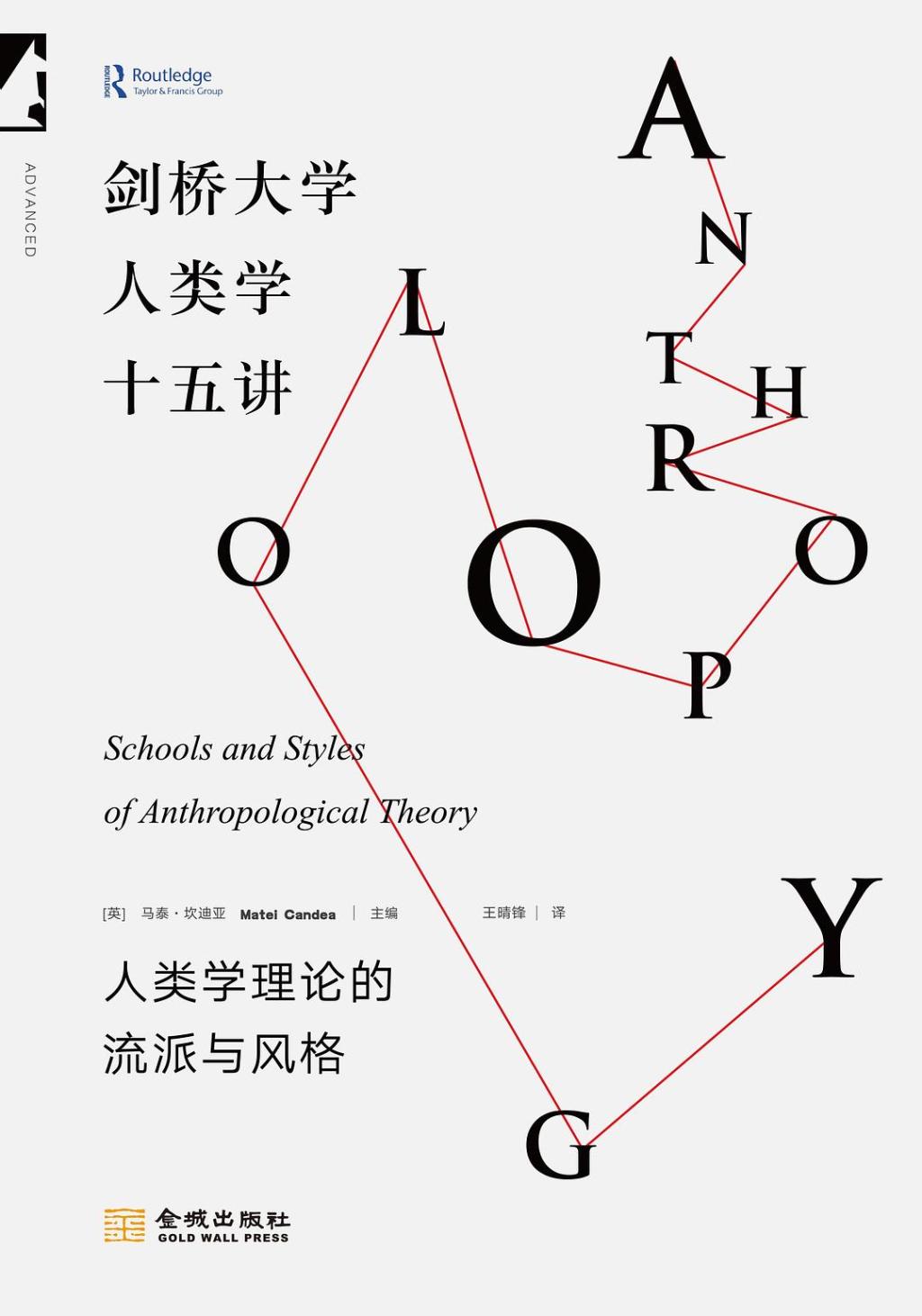
《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人类学理论的流派与风格》,[英]马泰·坎迪亚编,王晴锋译,金城出版社|领学东方,2024年8月出版,485页,68.00元
理论是什么
什么是人类学理论?马泰·坎迪亚(Matei Candea)在《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这本书的导言中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人类学理论的合集来源于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为学生开设的核心系列讲座,包含了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的诸多人类学理论脉络。编者坎迪亚希望将本书看作是参与讲座的人类学家,以及他们所介绍的人类学家们,共同对“什么是人类学理论”这一问题做出的多元回答。这意味着本书不仅提供对各种“理论”流派与风格本身的理解,而且要为“何为理论的本质”的讨论做出贡献。
坎迪亚认为,要回答“什么是理论”,或者说“什么是人类学理论”这一问题,需要从三个议题出发进行讨论。第一个议题,是理论与人类学中其他事物(方法、数据、实践等)的区别。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开始,或者说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初,方法与理论就密不可分。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并非对应经验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两个环节,而是相互挑战、相互启发,构成“不断进行的观念性革命”。但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意识到这种紧密关系不等于消解理论与方法或民族志之间的区别。当代人类学家和思想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也曾强烈反对将“民族志”泛化甚至等同于人类学(“That’ 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4, pp. 383-395)。因此,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间的关系应当视为有所区别但又互相启发的。
第二个议题,是理论内部如何划分。坎迪亚认为,用“范式”或“主义”的方式来划分,虽然突出了不同理论流派与风格的差异,但也会导致忽视各流派之间的潜在关联,甚至陷入将理论想象成线性进化不断迭代的误区。因此本书提倡一种更具历史性的视野,强调理论脉络的“复杂性、变化、转移、内部分歧与外部连续性”。在本书的第十五章,玛里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通过梳理关于“人格”(personhood)的争论,反思了人类学家构建和使用概念的方法。正如斯特拉森所说,人类学家总是在拾取各种概念和理论加以运用,我们需要在观念的流动中理解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
最后一个议题,是人类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间的关系。一方面,理论与田野工作之间的互补性张力、理论扎根于民族志情境的厚重性,是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人类学理论脉络显然受益于和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的跨学科跨对话,而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也反过来辐射到更普遍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本书关于“理论究竟是什么”的对话,不仅对人类学有益,也应当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启发。
人类学理论1:历史性的对话
正如前文指出,本书主张从一种历史性的视角去重新发现各理论流派与风格之间的联系。虽然不同章节的作者秉持不同的观点,但《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所谓“旧理论”的重视。包括编者在内的多位作者,都主张人类学是一门积累性的学科,那些被认为过时的、备受批评的理论,依旧可以激励和启发新的研究。
旧理论能提供的绝不仅仅是教训和告诫,通过重新发现旧理论的真诚和复杂,人类学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有益的遗产。例如,在第一章,坎迪亚认为十九世纪的进化论者虽然存在重要谬误,但他们论证方法的详细严密仍然值得敬佩,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奠定了二十世纪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基础,如对回避行为、婚姻居住模式等亲属制度,以及对万物有灵论和魔法、仪式的讨论(53页)。在第三章,凯若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梳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通过“生产方式”等有力的概念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带入人类学。虽然当今西方学术界几乎没有人类学家再使用六七十年代的那些范畴,但马克思主义显然深刻影响了经济、历史、亲属关系、女性主义等人类学重要领域的发展。再例如,第六章重新发掘了以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留下的扩展个案法。这一理论强调社会生活的突生性,通过追踪事件发展过程来研究社会关系的变动,对如今的人类学研究仍有借鉴价值,并且可以构成对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所谓“多点民族志”方法的反思与补充。哈里·英格伦(Harri Englund)也借此指出,现代主义的改革趋向总是试图抹除过去的痕迹,人类学理论需要警惕这种狂热,正视过去的理论遗产(248页)。而在第九章,克里斯托·林特利斯(Christos Lynteris)以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遗产为窗口,证明虽然法兰克福学派被普遍认为具有时代局限性,但批判理论对人类学来说仍然是有待发掘的潜在资源。在第十章,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梳理了米歇尔·福柯早期和后期著作对人类学的两种不同影响。事实证明,不同的人类学家出于不同的理论关切,基于不同的理论对话,总是能从福柯的著作中获得新的启发。
重新发现“旧理论”的价值,不仅因为它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应用于人类学研究,更因为它们是许多根本性观念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不同理论流派、风格之间关联性的梳理,有力地呈现了那些认识论层面的根本性矛盾——差异性与普遍性、人文阐释与科学解释、结构与主体如何影响一门社会科学的持续发展。
在第一章,坎迪亚考察了所谓“早期”人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扩散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共同构成了对进化论的反叛,它们之间存在着持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歧,但同时也共享着“有机体比拟论”的预设,即参照生物学观念将社会文化看作是由多部分构成的单元和实体。这种共同的反叛和共享的预设,证明人类学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是关系性的,而“正是在这些关系性的差异之中,才诞生了我们所知的人类学”(37页)。更重要的是,这些早期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为后来的人类学对话留下了诸多“二元对立”,例如理论建构与民族志描述、结构与过程、人文阐释与科学解释、单一案例的整体性描述与单一问题的比较研究、个体动机与社会文化机制等。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形成了理论对话中“有益的张力”,也是贯穿本书其他章节所述不同理论流派的重要线索。
例如,第二章就介绍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如何脱离第一章的有机体比拟论,开始将人类文化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符号系统。结构主义开启了许多人类学的讨论,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正如作者鲁珀特·斯塔什(Rupert Stasch)所说:“关于人类学家如何以各种方式脱离结构主义的描述,几乎也就是对整个人类学学科的描述。”(138页)因此,二十世纪后期的人类学理论流派,大多可以看作是围绕着与“结构”的对话,或者说对“结构”的反思而展开。第四章的交易主义、第五章的历史人类学,以及第六章的扩展个案法,通过将“过程”的历时性视角引入人类学,来反思“结构”的共时性分析;而第四章后半部分的实践理论,则始终致力于解决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第七章的认知人类学同样聚焦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是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社会性思维,转向了个体的心理与认知机制。
除了围绕着“结构”而展开的对话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学理论旨趣中对“特殊性与普遍性”“阐释与解释”的持续张力。对于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来说,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需要通过比较和归纳来解释关于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问题。而在第八章,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继承了博厄斯式的“复数文化”(cultures)观念,即不同的文化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它们内部整合而彼此间相对独立。这种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放弃了在全人类普遍范围内进行不同文化的比较、概括,更专注于对某一特殊田野案例的“深描”。而第七章的认知人类学,则是对这种只关注特殊性的趋向的不满,试图通过考察全人类共同的生物性基础——大脑活动,来找回早期人类学解释人类普遍性议题的使命。而在第八章内部,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格尔茨的批判,则延续了“主观与客观”这一社会学科脉络中更加经典且持久的认识论之争,最终落脚到究竟是否存在,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人类学真相”这一问题。后现代的批评者们指责传统人类学家的“作者本位”掩盖了民族志的主观性和权力关系,因此需要发展“对话式”和“多声部”的民族志。格尔茨则认为,“摒弃作者身份,让民族志主体和资料直接发声的想法,既是一种天真的政治幻想,又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对实证主义真理观念的留恋”(307页)。
这种贯穿人类学理论历史脉络的对立、矛盾、差异、张力,为一种持续的“对话”(dialogue)提供了基础。批判教育学者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强调,对话是所有为世界命名的人之间的相遇,是反思和行动的集合。将人类学理论整体视为一场跨时代的不断发展的对话,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不同流派间复杂多变的联系。再进一步,使我们能看清那些构成并支撑人类学理论的根本性观念争论(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并反思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我们批判性地对待人类学文本,将各种理论流派与风格视为不断展开的争辩,而非持续巩固的信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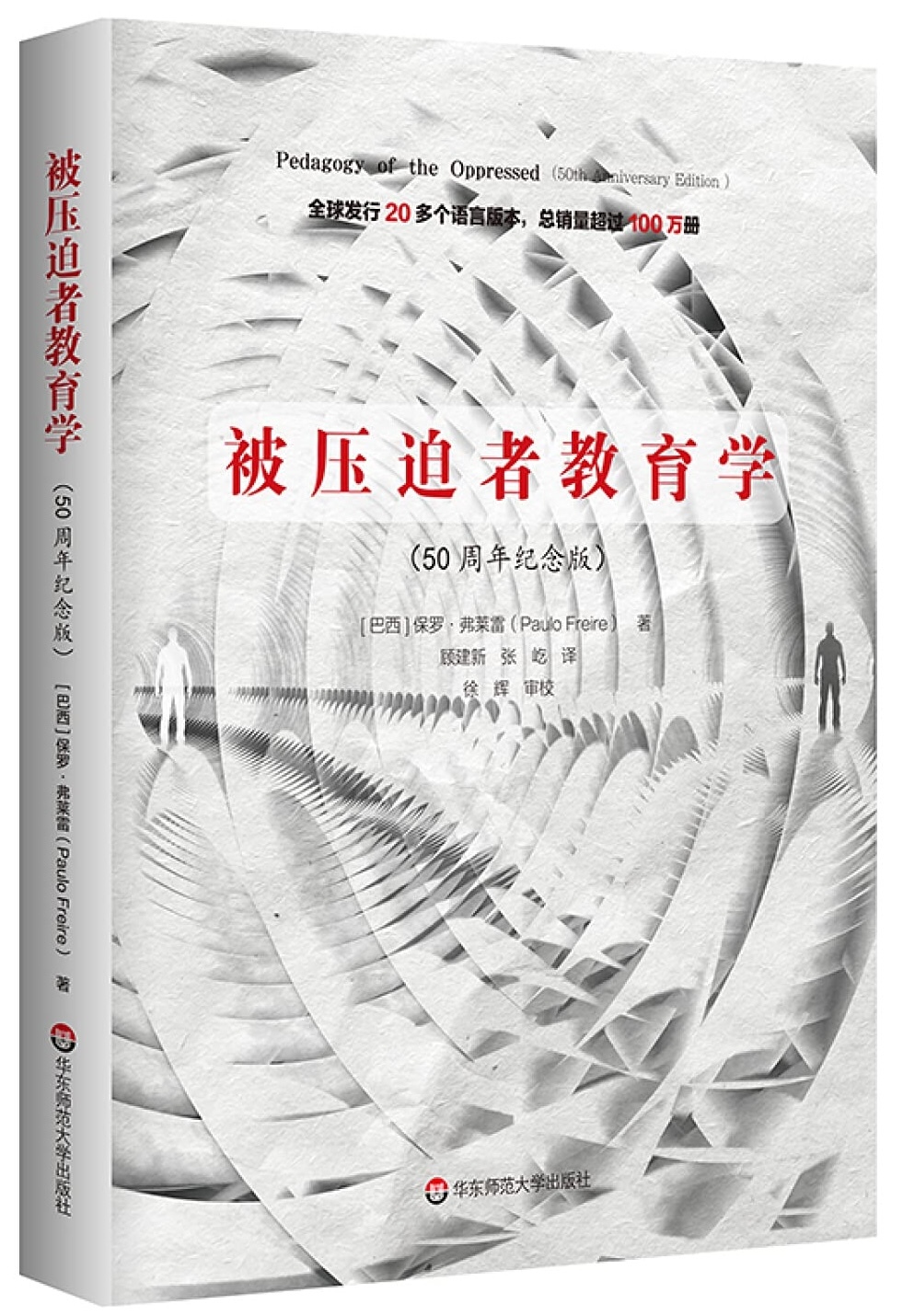
保罗·弗莱雷著《被压迫者教育学》
人类学理论2:关于世界的想象力
英戈尔德认为,人类学应该是两条相对弧线交织而成的椭圆,一条来自现实生活的教育,构成民族志,另一条则来自对世界观察性参与的想象力,构成理论(前揭,2014,p. 393)。在《规则的悖论》一书中,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引用五月风暴时刷在索邦大学墙上的标语“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来说明想象力与“幻想”不同,是一种能够参与影响甚至改变世界的力量(倪谦谦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77、86页)。英戈尔德意义上的理论想象力也是对世界的参与性改变,为了能够注意并且言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未曾认真关注和倾听的经验,人类学理论不断进行观念革命,发展出不同流派和风格,目的正是培养出各种各样对“世界是如何”的想象,并最终参与到对“世界应如何”的想象和实现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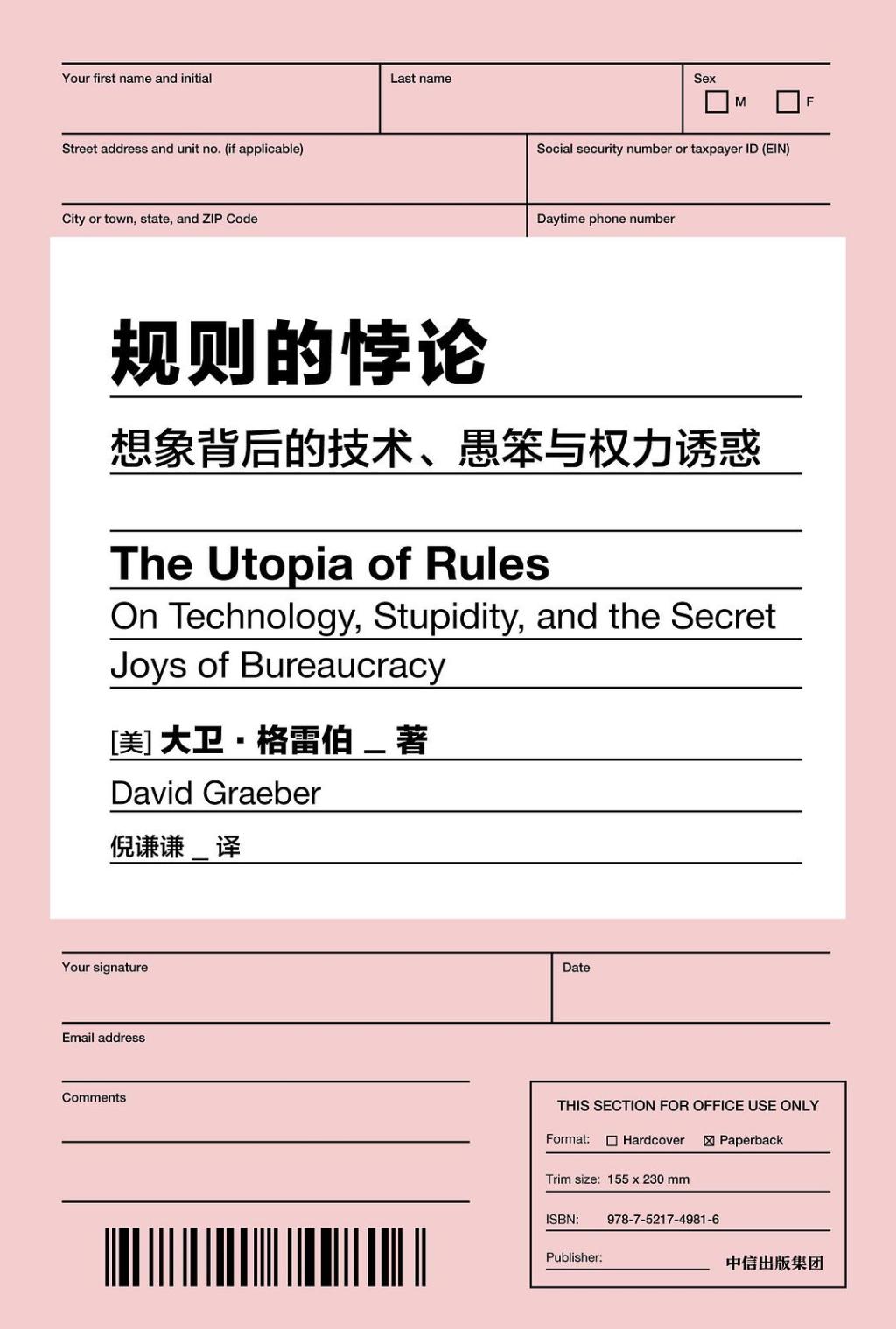
大卫·格雷伯著《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例如,第十一章讨论了人类学对身体的关注和重新想象。为了反对将一切想象为表征和符号,人类学引入了“具身化”(embodiment)的理论,使人们对“展演性和理解性的身体、作为行动者的身体以及作为生命体验的身体”投以新的关注。第十二章介绍了女性主义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性别研究。从1970年代时“开始思考女性”,将女性身份和性别不平等议题引入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到1990年代时,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提出以“反客观性的”方式来发展一种“女性主义的民族志”,以及朱迪斯·巴特勒通过展演理论更加激进地质疑一切性别二分的天然合法性。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人类学理论对性别身份和权力关系的重新想象在逐步深入,女性主义对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已经无可置疑。正如作者杰西卡·约翰逊(Jessica Johnson)所说,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很难想象一位人类学家的论述中会完全不考虑到性别的维度而不受任何质疑(403页)。作为一种寻求普遍解放的理论资源,女性主义带来的这种革命性的影响显然不仅存在于人类学界,而是遍布哲学、文学、语言学、政治学甚至生态学、神学等几乎所有领域。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在《女性主义全球史》一书中考察了在文学、心理分析和各种乌托邦构想中,对各种不同未来的想象如何能够揭示性别划分造成的暴力、荒诞与偶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如何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中表明,理论不应该是有距离感的抽象,而是对世界的参与,当我们以女性主义的方式去想象、去生活时,我们就是在做女性主义理论。因此,不论是人类学理论还是女性主义理论,都可以看作一种需要实践和参与,也能够对世界产生实质影响的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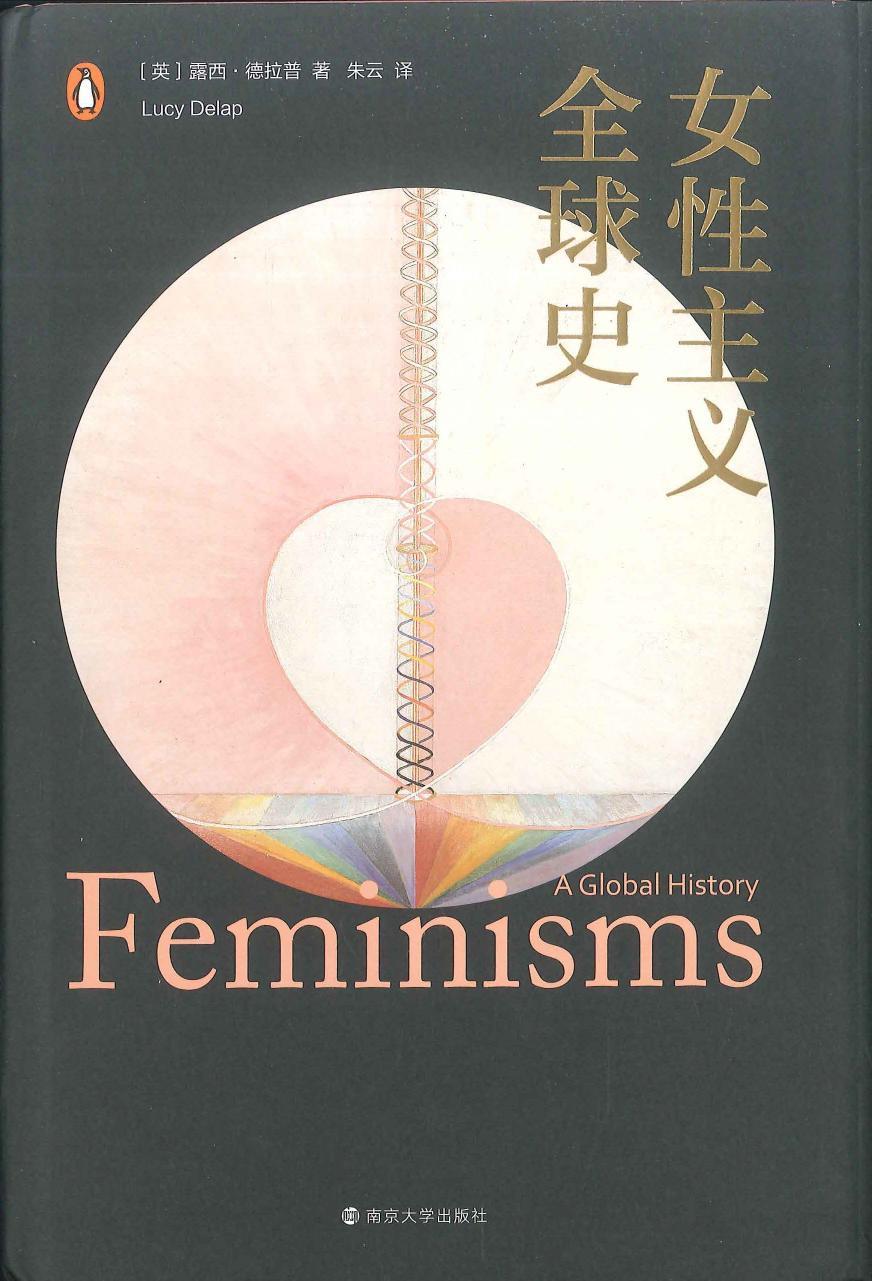
露西·德拉普著《女性主义全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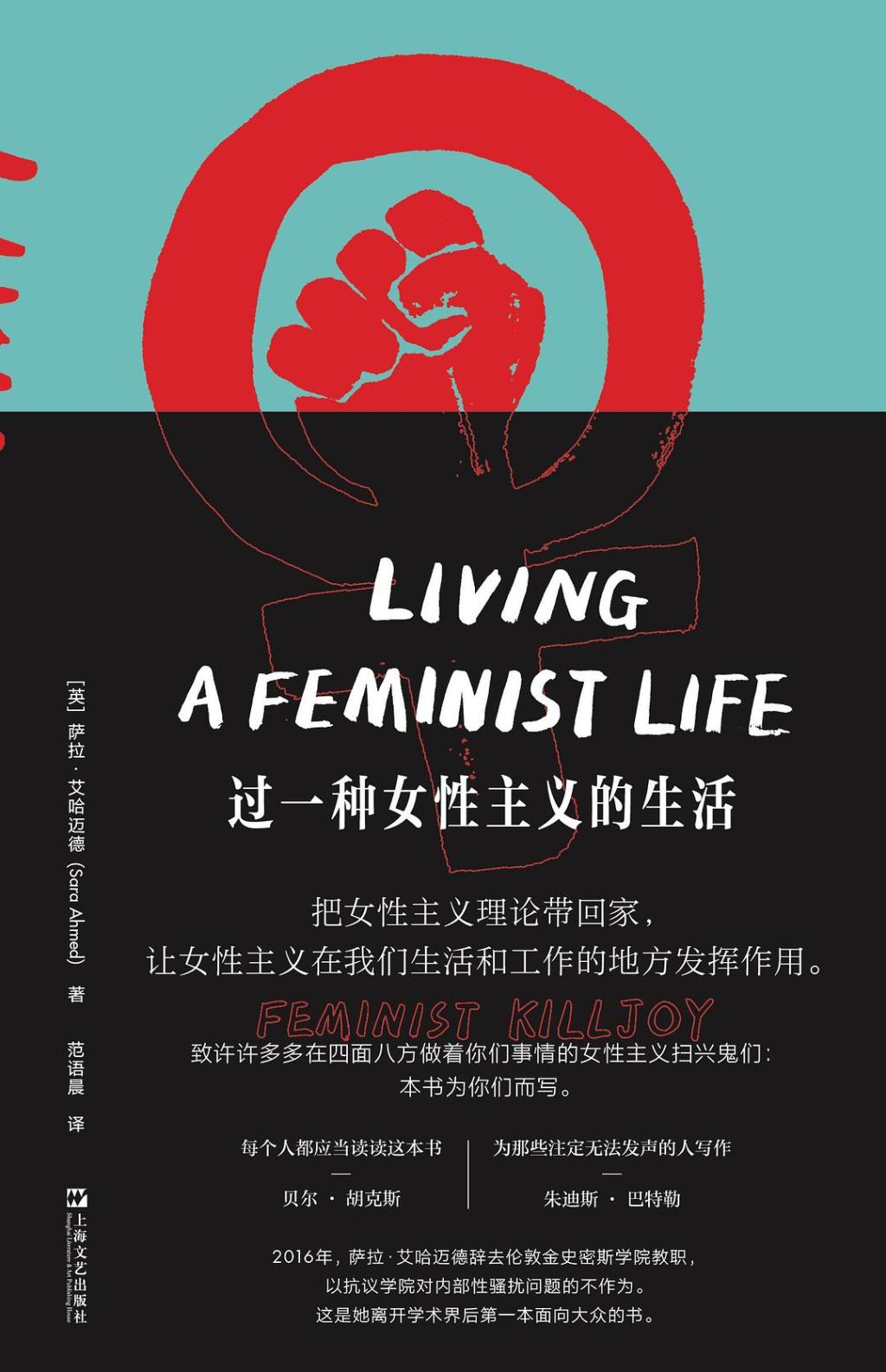
萨拉·艾哈迈德著《如何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
想象力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参与,更直观地表现在第十三章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第十四章的本体论转向,这两个流派都明确拒绝被归类成传统意义上作为知识体系的理论,而是将自身当作一种重新看问题的视角,一种用崭新语言工具重新理解世界、参与世界的尝试。在它们看来,每一种论述都是对世界的一种实践的或政治的干预,而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描述。以布鲁诺·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旨在想象一种将能动性扩展到非人类的世界,而本体论转向则要求想象一个拒绝物质与象征、自然与文化之间区分的世界。这两种理论的想象力提倡将它们的理论看作对思考问题方式的启发,以改变我们参与和影响世界的姿态,从而真正看见并重视各种“行动实体”和田野中遇到的“他异性”。这种大胆的做法受到了许多批评,包括适用范围无限延伸会导致分析变得模糊空洞,“启发而非理论”也被很多人类学家看作一种回避批判的托辞。虽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但这种将理论视为对想象力的启发、对世界的参与而非单纯分析工具的做法,无疑是对“理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全新回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后人类学思考和发展理论的方式。
最后,作为坎迪亚所说的“剑桥视角”,本书可以说是关于“百家争鸣”的“一家之言”,是有立场、观点、重点、局限的理论介绍(事实上所有的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本书必然无法涵盖所有人类学理论对话的脉络。例如,第九章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的介绍,只着重呈现了本雅明的理论资源,而没有涉及到哈贝马斯、霍耐特(Axel Honneth)、马尔库塞等重要学者的批判理论(对此作者也做了说明)。再如第十四章的本体论转向,并没有涵盖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多物种和赛博格的讨论,以及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关于语言问题和交际性的讨论,这两者对理解广义本体论转向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脉络。此外,试图重新想象人类生活和“世界是如何、应如何”的理论转向,除了本书提及的章节外,还有近年来不断发展的人类学伦理转向(ethical turn)。这一转向强调用伦理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学的所有研究议题,重新聚焦和想象人们对善好的复杂性追求。
人类学理论与教学法
坎迪亚在导言中表示,本书通过将人类学理论视为相互关联的历史性对话,试图教授批判性看待理论假设和用不同理论视角来分析经验材料的能力。对于所有从事人类学相关领域的人(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来说,本书都无疑是极为优秀的教材。乔舒亚·利亚申科(Joshua Liashenko)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人类学课程设计和教学法的论文(“Teaching Anthropological Theory: Reflections on Course Design and Pedagogy,” Teaching Tools, Fieldsights, November 15, 2022)中指出,理论不是学习并储存在脑海里的知识,而是一个持续参与的过程。在理论教学中,老师应当与学生一起“保持脆弱”(being vulnerable),拥抱被挑战的风险,向对话的可能性敞开。人类学理论的对话不仅仅是历史的,面向过去的,同时也应该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新的时代状况、生命经验、民族志发现,会持续不断地参与、挑战、反思、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对话。
对于非人类学专业的社科读者来说,本书呈现了认识论的反思如何影响一个学科中理论对话的展开,其中包括很多跨学科的对话。同样的主题也体现在其他人类学的教材中,例如亨丽埃塔·摩尔(Henrietta L. Moore)和托德·桑德斯(Todd Sanders)合编的人类学理论主题读本《人类学理论:认识论问题》(Anthropology in Theory: Issues in Epistem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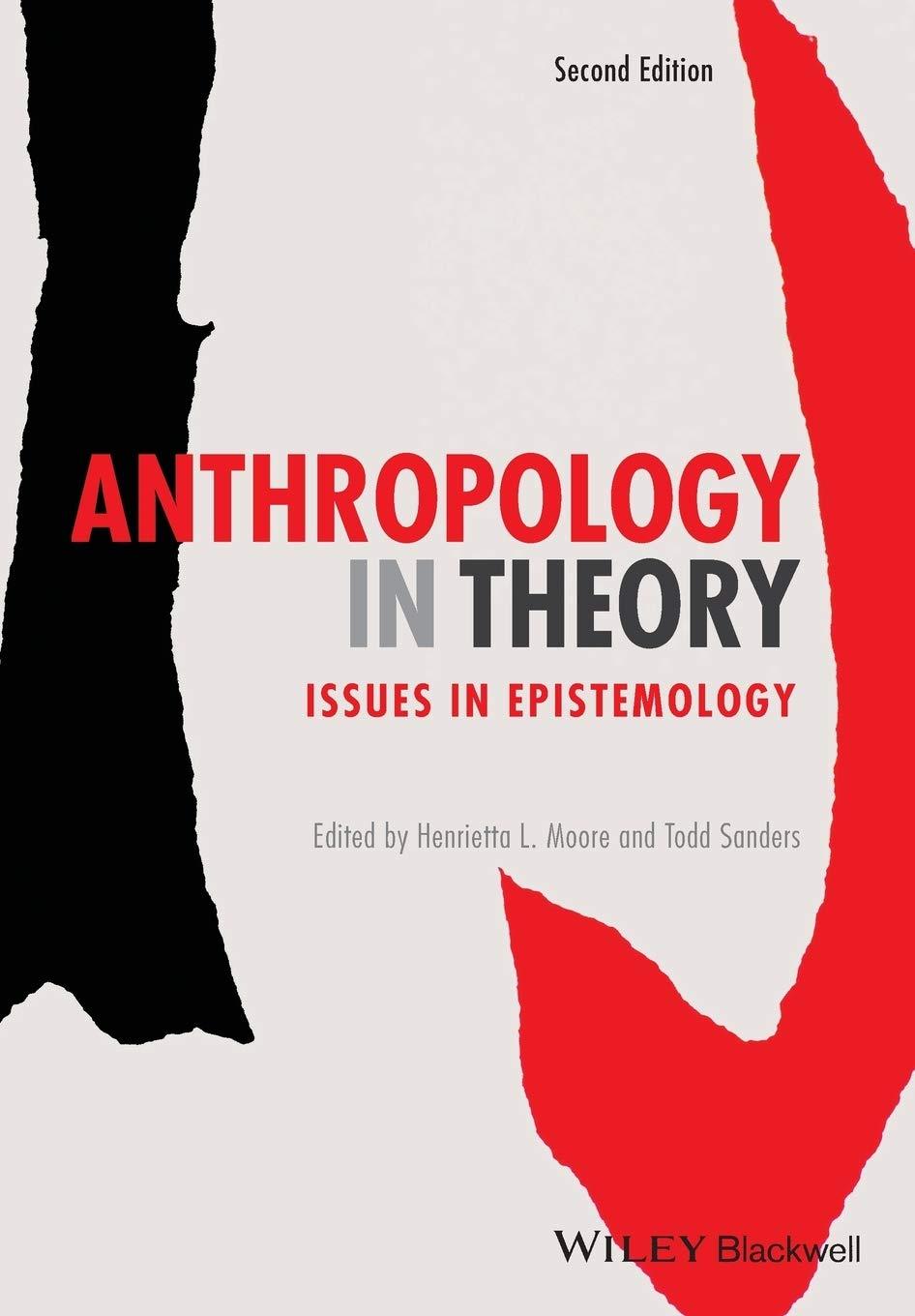
亨丽埃塔·摩尔和托德·桑德斯合编的《人类学理论:认识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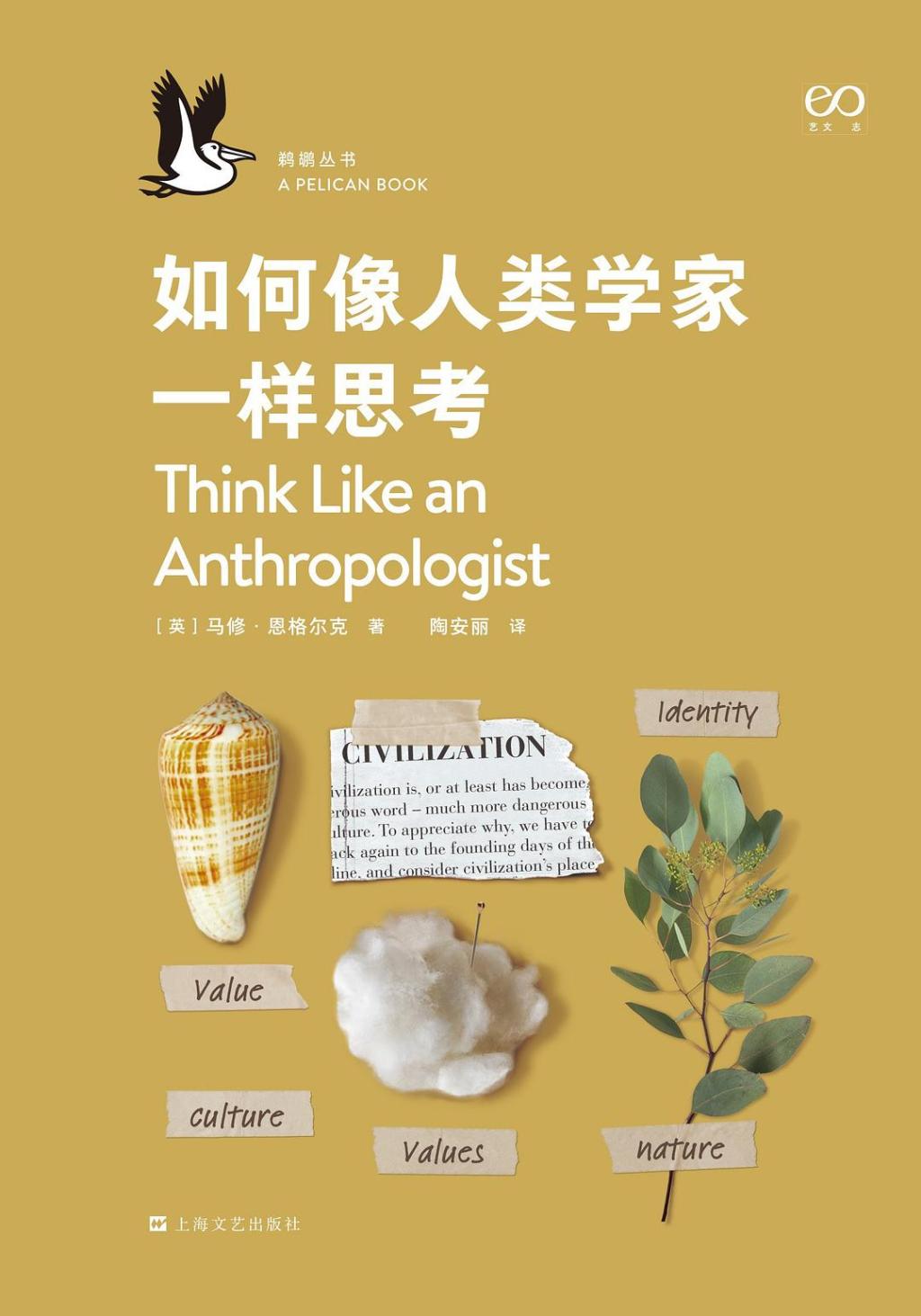
马修·恩格尔克著《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至于非学术领域的更广泛读者,本书也可以作为人类学通识教育的入门读物,它呈现了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与他者的世界相遇,并在相遇的经验中不断革新自我的观念,挑战并启发一种新的世界观。马修·恩格尔克(Matthew Engelke)在通识读本《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中指出,“让熟悉的变陌生,让陌生的变熟悉”,这种质疑和颠覆的过程是人类学的恒久价值之一。这两本书都强调了人类学之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即陌生经验不断被用来重新调整和改变这一学科的理论预设。在阅读人类学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需要颠覆常识,挑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并进一步反思我们认知的前提和方式。在今天,人类学这门学科乃至广义文科的存废问题被不断拿出来讨论,此时重新发现一种作为对话和想象力的理论并带着理论参与行动,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掘人类学知识的公共价值。








 冀ICP备15028771号-1
冀ICP备15028771号-1